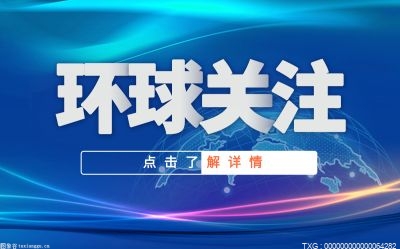来源:hao123百家号 时间:2022-04-26 20:41:23
2022年,中国的mRNA疫苗似乎正走进一个尴尬的境地。
4月初,石药和康希诺加入mRNA队伍,宣布旗下的mRNA新冠疫苗获批临床。习惯了“license-in”的云顶新耀,在去年从加拿大一家药企引进3款mRNA疫苗和平台技术后,也开始筹措成立一家mRNA疫苗公司。
新冠疫情两年后,中国的mRNA产业依旧不乏追捧者。从2020年起,资本疯狂涌入mRNA领域,与走在前头的美国市场相比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只是眼下,因为激进的审批政策、深厚的技术储备和mRNA疫苗的唯一性,mRNA技术已经在美国接连缔造商业传奇。而在中国,却不尽然。
截至2022年4月份,当国外药企都担忧新冠疫苗市场饱和时,中国mRNA领域打头阵的新冠疫苗却还未能获批。对于国产mRNA疫苗而言,当新冠这一“百年一遇”的机遇如指缝中的细沙滑落,市场处境是极为尴尬的。
“国内mRNA疫苗到现在还没出来,我觉得也不奇怪了,蛮难做的。”美国纽约Good Health Capital资本合伙人唐马克博士如此说道。
抛去政策等外部环境因素,究其原因,这批2019年前后才刚成立的中国企业,技术储备远不如十多年前就成立的Moderna和BioNTech。而mRNA技术本身的瓶颈,也让这批更多是跟随和微创新/地区创新(location innovation)的中国企业,不得不花时间交学费。
如今,一方面是估值高位运行;另一方面是海内外市场巅峰红利期逐步消失,中国的mRNA企业已经急需产品来验证技术成熟度,证实“我也能行”。
翻越“三座大山”,各出绝招
2019年,mRNA疗法公司在中国集中出现。前一年,Moderna刚刚登陆纳斯达克,创造了那一年生物技术公司最大的IPO记录。mRNA疗法也迎来了第一波高潮。
彼时,这些刚从海外归来创业的创始人都没能想到,就在他们公司成立不久的几个月后,一场新冠疫情将成为他们创业路上的一个大考。
尽管人类针对mRNA疗法的研究早在上世纪70年代便已开始,但直到新冠疫情前,尚没有一家企业能推出产品。而对于多数2019年才成立的中国企业而言,疫情的到来更像是背后的推手,让一个尚在学走路的婴孩必须立马跑起来。
而成败与否的关键之一,是技术储备到底能否支撑快速突破疫苗研发。
如果形象比喻mRNA技术——人类细胞若是“体内工厂”,那mRNA就好比“工人”。只要找到合适的“工人”,就能让“工厂”生产出自身治病需要的“药物”——特定的蛋白质。这意味着,如果人类能控制mRNA,将能随心所欲打造理想疗法。
理想很美好,但操作起来,却是关卡颇多。时至今日,mRNA疗法的三大卡脖子问题——序列设计、递送系统、放大生产,都形成了超高技术壁垒。而在mRNA的各个环节中,亦处处埋伏着欧美企业所设置的专利壁垒。
A. 序列设计
先看序列设计,这是各大厂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。
优秀的序列设计,可以更高效地表达抗原蛋白,最终提高mRNA疫苗激活特异免疫的精确性和活性。但这样的序列设计,要想产生并不容易,这个过程就好比写一本说明书,文字是各种氨基酸组合,目的是能借此“书”翻译成抗原蛋白。
问题是,这些氨基酸序列组合多达2.4×10的632次方个,假设人类每秒思考1个,直到宇宙结束或许都未能考虑完。
而AI的出现,就为找到最佳的方式进行翻译起到重要作用。斯微生物首席商务官张继国曾在一场演讲中指出,算法其实也是mRNA行业比较大的挑战之一。“你不能直接现在成立一个mRNA公司,去拷贝人家一个序列,这没有意义,因为大家的序列是不断升级的。”
眼下,各大厂商都需要有长期大量的数据积累,以此不断优化平台。Moderna的数据和AI团队,负责的工作之一便是自动化地完成需要由人类来完成的步骤和判断,如mRNA的序列设计。
而国内的斯微生物,在本月初与百度AI研究院再度合作,在现有算法基础上尝试开展环状RNA等序列设计迭代技术的开发。此前,双方已经就新冠mRNA疫苗的开发展开了AI序列优化算法的合作,开发了专门用于设计优化mRNA序列的高效算法。
事实上,完整的mRNA分子结构除了上述的序列设计外,其一前一后的5’端的加帽和3’端polyA尾同样重要。通过对这两部分的修饰,可以决定mRNA分子表达的效率。
但这样的技术,其发展重镇还是在美国等海外地区。有数据显示,仅以5’端的加帽为例,截至2021年4月,全球mRNA疫苗5’端帽结构技术专利中,美国申请的专利有128件,占比74.9%;中国仅有9件,占比为5.1%。
B. 递送系统
眼下,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,和序列设计相比,真正有挑战性的还是如何运输这本书。这就涉及mRNA技术的另一座大山——递送系统。
张继国曾坦言:“递送系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竞争力,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,递送系统可以占70到80分。”
目前,在递送系统上,主流方法是采用LNP(脂质纳米技术递送)。但围绕该技术,专利和Know-How是关键。三巨头中的BioNTech和Curevac都选择使用Arbutus的专利,而Moderna和艾博生物均为自主研发。
只是,Moderna败诉与Arbutus的LNP纠纷,已经业内皆知。从结果来看,发展如此多年的Moderna都避不开专利纠纷,国内新兴企业的情况亦是未知。
绕过专利的难度在于,Arbutus最初的LNP专利保护了较大范围的四种组成部分的比例,要想绕过就必须选择不同的成分,难度不低。但艾博生物创始人英博在一场演讲中曾表示,成分的专利是可以绕过去的,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美国公司知道这方面有专利,但还在用LNP技术的原因。
他认为:“LNP的专利其实并不是真正阻碍进入这个行业或者这个领域的门槛,知道如何突破这个专利,才是门槛。”
目前,诸如艾博生物、康希诺生物、石药集团等都是采用LNP。其中,艾博生物自主研发的LNP,其技术优势在于相较其他系统,核心阳离子脂质、蛋白表达高5-10倍,其他公司为2-2.5倍;而后两者作为非专注mRNA疗法的企业,亦都在前期做了一定的技术研发和储备。
2019年,康希诺就曾公开过一项用腺病毒作为递送载体递送自复制型mRNA疫苗(SAM)的专利,随后在2020年的5月份,与加拿大企业PNI合作,开发基于mRNA-LNP技术的疫苗。石药此次获批临床的mRNA新冠疫苗,有业内人士透露该疫苗亦是其自主开发,石药在上海有核酸研究所。
不过,即便是主流方法,海通国际表示,LNP在过敏反应、易氧化降解、制备重现率差等问题都仍有待解决。另外,以LNP为载体制备的mRNA制剂会在肝脏及脾脏聚集,但是难以靶向其他部位。
与大家都采用LNP不同,2016年成立的斯微生物,就有些“非主流”。斯微生物采用的递送系统是LPP。其官网如此介绍:“LPP (lipopolyplex) 纳米递送平台是一种以聚合物包载mRNA为内核、磷脂包裹为外壳的双层结构。LPP的双层纳米粒和传统的LNP相比具有更好的包载、保护mRNA的效果,并能够随聚合物的降解逐步释放mRNA分子。”
张继国曾透露,LPP递送系统巧妙地绕开了LNP的结构专利。其CTO沈海法在2015、2016年左右开始研发,2017年拿到专利。随后,斯微生物获得了该递送系统20年的全球独家授权。
事实上,研发新技术手段是一个未知的探索,并没有固定路径可以遵循。在昆山杜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黄林峰看来,这已经不是门槛或者壁垒,即可以翻越的问题;也并非钱就能砸出来。而是需要时间积累,外加一些运气或灵感。
“很多方法已经被实验验证过了。现在除了脂质体纳米颗粒载体,还没有看到更好的,至少是已经经过临床层面检验的递送系统。”他如此说道,“如果有很深的积累,至少能够领先且少走点弯路,但现在对于新方法怎么才能走到正路上,谁都没法说清楚。”
由于国内尚无有mRNA疗法产品获批,黄林峰和唐马克都认为目前尚无法对各家企业的技术成熟度下定论。“临床前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参考,但还是需要最终临床结果和数据来验证。”
而在黄林峰看来,递送系统接下来还要关注的两个问题:是如何去提高它递送的效率如mRNA本身释放的效率,以及找到副作用产生的原因。后者从mRNA疫苗诞生之初便备受关注。
C. 生产规模
最后一个卡脖子的问题,是放大生产。但时隔两年,在业内人士看来,扩大生产的技术难题已经都被逐步解决。
如今,原料的稳定性和质量问题,成为了黄林峰眼中更需关注的问题。“中国有没有能把原料做得跟美国那样好的,还是个问号。”要知道,在两年前,因为mRNA的产量暴增,上游不少供应商都反应不过来。有业内人士透露,前几个月,连符合GMP的DSPC(磷脂酰胆碱)都买不到。
据海通国际测算,加帽所需原料、修饰核苷酸及质粒是供应链生化材料最核心的三部分,成本分别占比31%、20%、9%。其中,太平洋证券测算,酶是最重要的原料,也是价值链最大的一块。比如,加帽酶就非常昂贵。该机构预计,10亿剂mRNA疫苗将带来60-70亿元的酶相关需求。
目前,mRNA药物核心生产仍以海外为主。海通国际表示,国内部分公司如金斯瑞在质粒生产领域、恺佧生物、近岸蛋白、诺维赞等在加帽酶领域、兆维科技、糖智药业在修饰核苷酸领域、迈安纳在LNP生产设备领域已经取得领先地位。而各家厂商也都与上述企业有所合作。
“大家都还在努力攻克难题,但有多少积累、有多少技术储备?这是不是能够靠砸钱就能做出来,仍然是问号。”黄林峰说道。这成为了现下所有中国mRNA疗法公司必须直面的问题。
但不可否认的是,黄林峰和唐马克都感觉,总体而言,国内技术相比国外仍有差距,目前更像是在跟随和微创新。
接不住的“百年一遇”机遇
技术储备的差异,造就了世界的参差。
事实上,在mRNA新冠疫苗之前,全球都尚未有一款mRNA疗法获批。而中美两国几乎同一时间起步的mRNA新冠疫苗,如今已经走向两个不同境地。
2020年春天,当BioNTech/辉瑞和Moderna宣布研发生产mRNA疫苗时,复星医药也从BioNTech引进了疫苗。那时,斯微生物和前一年刚成立的艾博生物,同样启动了新冠疫苗研发项目。
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,国外mRNA新冠疫苗研发“好比边航行边造飞机”的进展,极大刺激了国内。当mRNA这项新技术点燃了产业热情,大药企和资本都争先恐后“抢”起了标的。
2020年5月份,沃森生物与艾博生物达成了合作开发mRNA新冠疫苗的协议,一个月后,该疫苗便获批临床试验,成为国内最早获批临床的mRNA疫苗。
同一个月,眼看沃森生物牵手了艾博生物,西藏药业也选择了斯微生物。要知道,根据媒体报道,艾博生物团队只有9个人的时候,斯微生物已经有200多人,而且在1月份就对外宣布要开发新冠疫苗。
只是在这场拉锯战中,原本被认为会“遥遥领先”的斯微生物,却逐渐落到了后面。2021年1月份,斯微生物才宣布mRNA新冠疫苗获批临床。随后,第三位选手丽凡达在3月份也宣布产品获批临床,2个月后,这家企业就被艾美疫苗收购了。
而在这期间,智飞生物入股深信生物、君实生物投资嘉晨西海,后者还同时与三家药企开展合作,都成为了当时备受瞩目的新闻。
在唐马克看来,当一项新兴技术刚开始发展时,biotech与大企业的合作无疑是个明智的选择——一个背靠大企业好推进临床和布局销售渠道,一个借机入场mRNA疗法新兴领域,看起来是一场双赢的结果。
但不同于其他家,斯微生物与西藏药业牵手的结局却以悲剧收场。2021年8月份,或许是斯微生物觉得西藏药业在疫苗布局上却有所欠缺,或许是西藏药业因斯微生物的mRNA疫苗进展太慢,总之,西藏药业放弃了这项合作,只是股权投资。
天下熙熙皆为利来。就在传统药企接二连三入局时,资本也从未停歇。2021年开始,斯微生物和艾博生物不断获得高额融资,夸张时,一年的融资次数就至少两轮起。
有媒体统计过一个数据——2021年,mRNA技术的全球融资总额超过17亿美元,而中国,就以超15亿美元占据90%。其中,资本宠儿——艾博生物总计10.2亿美元的两轮融资间隔时间仅有3个月,自研的mRNA递送技术成为其核心卖点。
不过,产业的热度似乎跟结果并非正相关。
当Moderna和辉瑞赚得盆满钵满——在美国,mRNA新冠疫苗让辉瑞过去一年营收增长92%,再次重回全球第一制药企业宝座。Moderna更是从无产品收入到销售额实现175亿美元,甚至出现新冠药物过剩担忧时,中国的mRNA企业,却在过去两年不断获得高额资本投入后,迟迟未能推出产品。
究其原因,过去两年,mRNA疫苗能在美国成功而非他国,完全契合了“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”和“时势造英雄”。
“美国做对了两件事,第一件是加速审批。在临床数据并不完美比如副作用明显的情况下还加速批准,这在平常是不可能实现的;第二件是规模化生产的成功。”黄林峰说道,“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。工业发达和创新能力强,让他们得以在短时间内实现这个工程化的成功,保证全球供应。这本身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。”
但这些,都尚未能在国内看到。而随着其他技术路线的新冠疫苗开打,mRNA新冠疫苗的临床资源和市场份额都不可避免受到影响。不过,随着中国开始部署新冠疫苗序贯加强免疫接种,即间隔接种(交替接种)不同技术路线的疫苗,或许能为mRNA新冠疫苗争取一些生机。
目前,国产mRNA新冠疫苗进入“决赛圈”的,仅有艾博生物/沃森生物和复星医药/BioNTech两家的产品。前者今年1月份刚披露Ⅰ期临床数据,且国内Ⅲ期临床的现场工作基本结束,正在进行数据整理和持续血清检测。后者自去年起,尽管不断公开表示马上要获批了,但已经卡在行政审批上迟迟未见结果。
此前,一些业内人士表示从临床数据来看,艾博生物/沃森生物的产品表现低于预期。对此,唐马克表示,“目前来看,更像是me-too吧,当然我们希望最好不要是me-worse。”
mRNA疗法的好日子还在后头
一边产品“难产”,一边估值高位运行,以致于不少人担忧会不会期望越高,失望越大?种种迹象,也给市场敲了一记警钟。
唐马克认为现在mRNA领域已经有所降温。但据不具名的投资人士来看,该行业依旧炙手可热,一些投资机构仍在寻找好的标的。
只是,从入局的方式来看,他们已经更倾向于在B轮以前进场,尽量避开一些风险。唐马克亦表示:“如果是早期投资还可以,等到后面再进场,因为企业估价金额确实很高,很容易被套。”
眼下,后入局者依旧颇多,不少企业仍揣着门票巴巴等着搞起mRNA疫苗——2022年,在去年从加拿大公司引进mRNA疫苗和平台技术后,云顶新耀和华润医药准备着手成立一家mRNA疫苗公司;石药和康希诺凭借mRNA新冠疫苗获批临床,正式加入mRNA疗法竞赛;安科生物宣布进军新冠mRNA疫苗;荷塘生华也与翌圣生物正式达成战略合作,一起打造mRNA药物研发、生产新生态……
只是,随着新冠肺炎疫苗市场逐渐饱和,这些赛道里的玩家也需要寻找新的机会。
黄林峰认为,所有的mRNA厂商要想实现高收益,还需要开拓国际市场。无一例外,出海成为了各大厂商大力布局的方向。
此前沃森生物的投资者交流记录显示,身处决赛圈的艾博生物,其与沃森生物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联合开发的mRNA新冠疫苗正在墨西哥、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开展Ⅲ期临床效力试验,现处于病例收集阶段。沃森生物也表示,为支持印度尼西亚合作方本地实施新冠疫苗产业化的计划,将提供部分新冠mRNA疫苗原液用于其产业化建设过程相关验证。
只是,“怎么跟国外的同行在价格和效果上竞争?这也是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。”黄林峰说道。
与此同时,走在前头的公司,已经在继续探索新冠疫苗后的下一个市场。
BioNTech刚发布了CAR-T+mRNA疫苗治疗实体瘤的临床数据。辉瑞和赛诺菲则都同步押注了mRNA流感疫苗。该领域被视为mRNA疫苗的下一个高地。
反观中国,路径亦是相似的。唐马克指出,某种程度上而言,在mRNA疗法领域,美国的现在就是中国未来的方向。
艾博生物创始人英博也曾表示,mRNA疫苗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会集中在肿瘤和传染病疫苗、罕见病等。眼下,艾博生物与沃森生物还将合作开发带状疱疹mRNA疫苗。斯微生物的mRNA个性化肿瘤疫苗则在今年2月中旬进入海外临床阶段。
黄林峰认为,再往下走,便是基因治疗了,即探索能不能取代现有的、以病毒类为载体的基因疗法。而这正是Moderna一直在做的事情。去年年底,Moderna宣布与基因编辑初创公司Metagenomi合作,将该公司基于CRISPR的下一代基因编辑系统和其他基因编辑系统与其自身的LNP技术等相结合,以此开发下一代体内基因疗法。
“Moderna和BioNTech为中国企业建立了一个标杆。”唐马克说,“mRNA疫苗的市场是不会消失的。但我们不免会好奇,全世界有这么大的市场,有一天,中国的这些企业会不会做得更好?
黄林峰很难想象,未来在中国会有很多家mRNA公司同时成功。他认为,只有拥有独特技术的公司才能够成功。而独特技术,是要看市场和产品来检验的,并非是几张宣传的PPT就能看清。
但无论现阶段资本是否更多是在跟风,无论热钱涌入和产品尚无上市的尴尬是否还将持续,黄林峰与唐马克都一直坚信,mRNA技术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标签:
- 新地标!漳州不夜城正式开建|每日快报
- 看热讯:我乘着风的翅膀去飞翔是什么歌
- 总是执着等待爱情的到来是什么歌
- 动物取名大赛是什么意思|环球速看
- 大学生特种兵式旅游是什么梗
- 长月烬明OST阵容有哪些-世界热推荐
- 学生八字刘海怎么剪(学生八字刘海怎么剪教程):环球今亮点
- 萨莫吉尔尼(关于萨莫吉尔尼的简介)
- 新西兰央行加息50个基点至5.25%
- 当前快播:电解液“龙头”一季度净利润或“腰斩”
- 硬核快报 | 最不皇冠的CrossSport 有哪些新技术?
- 世界热门:【这些文化遗存现今的模样41】这才是鱼米之乡应有的滋味!
- 清明假期南宁车站加开多趟动车,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
- 黄菡:为节目站台6年,因女儿不得不离开,如今怎么样了?|全球新消息
- 热消息:七夕你送什么给你男朋友了
- 突发!一中国百强大三甲主任被带走!|天天观速讯
- 4月05日18时新疆阿勒泰今日疫情通报及阿勒泰疫情患者累计多少例了
- 宁科生物最新公告:济南长悦违约导致子公司中科新材临时停产
- 华纳兄弟100周年,将在北京展映《卡萨布兰卡》等经典电影-世界快资讯
- 文科男生热门专业排名前十名_男文科生热门专业|环球今热点
- 佳沃食品(300268.SZ)获惠通基金增持22.37万股 持股比例增至5.02% 世界今热点
- 天天报道:文成这个护士长获奖!恭喜你
- 清明扫墓客流迎来高峰-热点聚焦
- 甲基异丁酮MIBK商品报价动态(2023-04-05)
- 非洲版《火影》来了,鸣人暴露本性,小樱是你讨厌的样子:当前播报
- 重庆北车站派出所组织青年民警开展“清明忆英烈”主题活动|世界今热点
- 当前快看:使用小程序快速解决家中电器故障的问题
- 带上这本书去看大熊猫-每日精选
- 历经4年风雨,波音能否冲破云霄?还有138架中国客户MAX待交付
- 天天亮点!庆余年手游如何出师 庆余年手游师徒玩法介绍
- 视讯!五点式安全带图片_五点
- 今年5月—9月 重庆高温天气较常年偏多 热文
- 那不勒斯0-4AC米兰:技战术配合更胜一筹仍难免输球
- 酷冷至尊高刷显示器新品特价仅需599元
- 环球快资讯丨程莉莎把自己的耳环给婆婆戴,蹲下给婆婆穿鞋,婆婆的回应显情商
- 【环球聚看点】网店怎么开,大概需要多少钱
- rua是什么意思网络用语
- 清明节为什么都是4月4号或者5号
- 环球快消息!清明节为什么是公历不是农历
- 2023年最火戏腔古风歌曲有哪些
- 英雄之光丨春晖万里 山海相逢——贵州籍抗美援朝烈士亲属到沈阳祭扫英烈侧记
- 快资讯:科创50暴涨,起因经过与结果全面解读,以及买哪个基金?
- 世界今热点: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聘书怎么写_会计专业技术职务聘书
- 消失的搭车人攻略_消失的搭车人攻略
- 每日消息!中国十大成人用品批发市场进货渠道在哪里
- 广州最大批发鞋城鞋子市场在哪里 天天实时
- 青年大学2023年第7期答案最新版分享:天天看热讯
- 百事通!搞笑泥浆去尿是什么意思梗
- 2023年十大抖音最火的歌曲是什么
- 时代变了,《千古玦尘》原著作者也开始磕男主和男二CP了_滚动
- 每日速讯:豆芽如何清洗干净 怎样清洗豆芽
- 直播卖衣服货源哪里找-今日观点
- 政府部门的财务报表有哪些_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应当不包括_ _全球热门
- 真锅明良
- 直播带货进货批发网站哪个好
- 全球观焦点:利润大的倒卖项目:倒腾什么二手货最赚钱
- 焦点热讯:河南:创新载体展示“大美学工”育人风采
- 环球最资讯丨周知!阳江殡葬机构清明期间停车指引
- 名宿:不相信梅西会重返巴萨,这不符合球队在竞技层面的利益
- 如果爱忘了泪不想落下是什么歌
- 盘点2023年最火的十首歌:速递
- xxn是什么意思的缩写|全球即时看
- 泰坦三勾是什么意思梗
- 世界头条:隆鼻手术恢复期多久,隆鼻手术风险有多大
- 全球今日报丨2023天津红香酥梨园游玩攻略
- 2023年抖音流行歌曲排行榜 天天即时看
- 你觉得已经够顶了我说还不算是什么歌
- 神田钛锅:绿色健康、经久耐用,成钛锅品牌首选产品
- 如何喷漆电子产品_送给爸爸的最佳礼物是什么 世界观察
- 人气爆棚,安琪亮相武汉良之隆食材展 资讯推荐
- 古船食品拟转让青岛古船80%股权及4018.54万元债权
- 海欣食品拟受让东鸥食品51%股权,并对其增资1020万
- 每日简讯:安琪参加第六届中部地区水产饲料实用技术论坛
- 太极集团04月04日继续上涨,股价创历史新高
- 红谷滩区关停29家无证校外培训机构:新视野
- 抖音流行歌曲2023最火前十名|每日消息
- 吴京被电击是什么意思梗
- 环球视讯!纸嫁衣5什么时候官宣 纸嫁衣5上线时间最新消息
- 嘀嗒出行实时路况在哪里开启
- 潢川县林茶局:立足林业工作职能 多措并举优化提升营商环境_世界新动态
-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的意思_如何解释成大事者不拘小节
- 微店在哪里?微店是怎么搜索店铺的_天天快资讯
- 要闻:2023年5月嫁娶黄道吉日一览表
- 网络用语sfsg是什么意思
- 微资讯!揭秘你不知道的寒食节是怎么来的
- 张丹峰洪欣现状如何离婚了么 张丹峰洪欣年龄多大
- 推特“小蓝鸟”标志变“狗头”! 马斯克又“搞事情”? 今日关注
- 清明节可以发红包吗 热资讯
- 2023五一节法定假日1天还是3天_世界快讯
- 天天新资讯:尘肺病会导致肺部纤维化吗
- vhd文件有什么作用 VHD是什么有什么作用有哪些优点
- 2023五一期间可以领结婚证吗-今日快讯
- 每日讯息!太空殡葬是什么意思?中国公司将推出“太空殡葬”怎么回事
- 【播资讯】奥德彪拉香蕉音乐叫什么
- 清明节高速几点会堵车?2023年4月4日5日高峰期时间预计几时:全球时快讯
- 太空殡葬要多少钱?太空灵位最便宜1.98万元起
- 漳州妇联为漳州国寿授“巾帼文明岗”奖牌 全球最资讯
- 口诛笔伐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读_口诛笔伐是什么意思
- 关注:好摇不挑曲是什么梗
- 全球热推荐:要是妳不在我不在心不开我进不来是什么歌



烹调鸡蛋常犯哪些错误?鸡蛋正确的烹饪方法有什么
- 你好!厦门!我是多多邦手作工坊!
- 选对番茄酱=拿捏住了意式披萨的灵魂
- 瓦匠驿站岩板标准化铺贴课程:现场交付 \ 一岩到底!
- 方言之下有新机 大胆说出你家乡的方言
- 比亚迪发布e平台3.0:打造闭眼买,放心开的智能电动汽车
- 性感本人杨天真再玩跨界,无视问号自信就完了
- 换季感冒易频繁,儿童备药技巧分享
- 零氪科技李丽平:单病种数据队列助力药企突围“内卷”困境
- 全球知名真实世界研究专家冯胜博士加入零氪科技 任首席数据科学家
- 手机色彩影像进入新时代?OPPO Find X3率先发力!
- 零氪科技:药品谈判“降价超5成”背后-中国真实世界研究迎来“爆发”
- 爱尔眼科医院可靠吗?绕开这3个危险因素,近视离你远一点
- 零氪科技张天泽:混沌中找确定性机会,看这三点 |亚布力青年说
- 进入国家旅游业第一方阵!建业集团荣登“2020中国旅游集团20强”
- 进博会 | 零氪肿瘤数字疗法亮相 现场签约入驻无锡国际创新园
- 准妈妈们:除了唐筛,甲状腺也要查,事关宝宝智力!
- 【双十一必看攻略】最值得入手的智能门锁,从这里面选就对了!
- 创新三位一体协同“作战”模式 蒙牛助力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
- 阿勒泰“双创”孵化基地新闻发布会
- “歌声中的历史”—郑律成作品音乐会